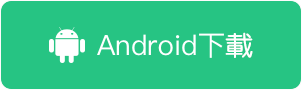蕭晟旌雖然暫時讓燕國皇室一族不必像階下囚一樣關在監獄裡,可是還是在他們的住處派了重兵把守——畢竟這些人身份等閒,不能出一點兒差錯。
另一方面,蕭晟旌早已將自己的親筆書信快馬加鞭送到鄭國國君鄭松德手上——若是不耽擱,三日便可到他手上。
那一封披星戴月要送到鄭松德手上的書信,是蕭晟旌言辭懇切的請求:燕國小國寡民,願歸順鄭國,從此以鄭國馬首是瞻,絕無二心。況且,燕國距鄭國有些距離,此後也不好管理。權衡之下,不如讓做了藩國,也省了許多力氣。
至於和長歡公主的婚事,也直接在燕國舉行,等回到鄭國的時候,再行一遍大禮。
「王爺,奴才可真是不明白了,」小廝興兒一邊幫主子磨墨,一邊小聲嘟囔道:「我們原本已經破了燕國,燕王都朝您下跪了,您不鳴金收兵,威風赫赫地班師回朝,卻偏要多此一舉,這麼一來,您的功勞可不就大打折扣了嗎?」
興兒說完後,打量着座上的蕭晟旌,見他沒有動怒的神色,心裡稍稍放心,又忍不住多嘴道:「奴才瞧着那位公主也沒什麼好,看您的眼神像刀子似的,京城裡好看的姑娘多的跟米粒兒似的,您怎麼就這麼想討她好?」
說到這兒,蕭晟旌才抬眼,將手裡的《沉疴記》不輕不重地合上,皺緊了眉頭,語氣頗為不悅:「這半晌了,墨沒磨多少,話倒是說了一籮筐——我這裡用不着你,你若是無事,就去替本王看看大婚的東西準備地如何了,順便再去瞧瞧燕王。」
「是。」興兒挨了罵,不敢再多嘴,懨懨地離了書房。蕭晟旌難得得了安靜,繼續翻卷閱覽。
只是,不出半個時辰,興兒又跑了回來,打開門衝進書房,「撲通」一聲跪在蕭晟旌面前,面色如土,連話都說不全了。
「出什麼事了?」蕭晟旌第一反應,就是看向東廂房的方向——那是長歡的暫時住所。
「是、是燕王!」興兒哆哆嗦嗦地抓住自己的衣衫,驚恐失措地喊道:「燕王他上吊自盡了!」
興兒原本是奉命去看燕王的,誰知道到了住所,瞧見裡面黑燈瞎火的,聽不見一點兒聲音。天寒地凍,守衛的人也去偷懶,四下沒有一人。
他原本打算回去,又鬼使神差地叫人打開了門,誰知道一踏進門,就瞧見房樑上吊着一個人,面色發青,嘴唇吐出來老長,一看就死絕了。
「死了?」蕭晟旌站起來,又問道:「公主那裡知道了嗎?」
「此時非同小可,當時有許多人都看見了,想必早已經傳到了公主的耳朵里。」興兒跪在地上,驚魂未定。
蕭晟旌頓了頓,將手中的古書丟在一邊,快步來到了東廂房,可是,守在門口的小丫鬟卻哭着稟告,說她一時沒有看住,長歡就在剛剛跑了出去,也不知道去了哪裡。
蕭晟旌臉色更加難看,但是也沒有說什麼,回身準備往燕王的住處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