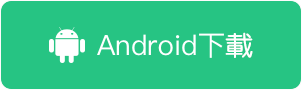夜裡,雨雪愈發下的大。逆風而行,侍從手裡的紙燈籠不出百步便被吹熄,實在艱難。好不容易到了燕王的住處,蕭晟旌的鞋襪已經濕透了。
興兒心疼極了自家主子,正準備上前勸告,卻見蕭晟旌站在流瀉出的昏黃燭光中,堅毅的臉有一半陷在陰影里,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悲涼。
一時間,興兒也不敢多說什麼,安安靜靜退到一邊,等着主子的吩咐。
蕭晟旌在門口停了停,抬腳跨過門檻。
燕王的屍體已經被安置到床上,蓋着厚厚的錦被,看上去如同睡着了一般。
青磚地上扔着一把泛着寒光的寶劍,劍刃上沾着幾點鮮血。
長歡後背挺得直直地跪在床邊,聽不見一點兒啜泣聲。
蕭晟旌的腳步忽然有些慌亂地停在原地,不再上前一步。
方才一路趕過來落在肩頭的雪花,此時此刻已經融化,雪水緩緩滲入肩頭,蕭晟旌恍然未覺,緊縮眉頭,看着長歡的背影。
「本王會將燕王厚葬,」沉默片刻,他又補充道:「依照國君的禮儀制度。」
那單薄的背影依舊紋絲不動。
空氣中還瀰漫着血腥氣,蕭晟旌又望了望床上早已僵硬的燕王,上前一步,伸出手,不由分說地將長歡從地上拉起來。
幽暗的燭火下,將長歡臉上的淚痕照得清清楚楚。
蕭晟旌的手不由得鬆了兩分:「人死不能復生,再多眼淚,也不能將燕王從閻羅殿哭回來。」
跳動的燭燭火映照在長歡絕美的臉上,猶如鬼影。
長歡的目光猶如利刃,將蕭晟旌的肌膚一刀刀剜下肉來。
「王爺的心意可圓滿了?」
長歡清寒的聲音在蕭晟旌耳邊響起。
話音剛落,長歡便掙脫了蕭晟旌的鉗制,撿起地上的長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將劍橫在蕭晟旌的脖子上。
「你覺得燕王是我殺的?」
蕭晟旌單手碰了碰劍刃,寒意侵骨。
長歡默不作聲,只是把長劍又推進了兩分。
他不殺伯仁,伯仁卻因他而死。是與不是,又有什麼區別?
蕭晟旌的脖子上已經有了血痕,若是長歡在繼續下去,他恐怕就要下陰曹地府,和燕王作伴了。
門外,興兒和剛剛趕來的侍衛膽戰心驚地守在門外,望着沒有一絲動靜的房間,恨不得下一刻就衝進去。
只是,蕭晟旌卻沒給他這個機會。
「三年前的雪,也是下得這樣大。」蕭晟旌似是笑了笑,將目光轉向糊了明紙的窗戶。
「你沒有資格提。」
三年前的那一夜,成了長歡避之不及的禍根。每每想起,長歡便悔恨不已。
但是,她不願意想起,可是卻偏偏有人要她到死都忘不了。
手腕兒忽然一陣劇痛,長劍「噹啷」落地,等回過神來,長歡已經被蕭晟旌反手押住,臉直直地往燕王的屍體上湊。
「口口聲聲說我是殺人兇手,那您這個救下了殺人兇手的公主,手上又有多乾淨?」
蕭晟旌的聲音驟然狠厲,不由分說地將長歡的粉飾撕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