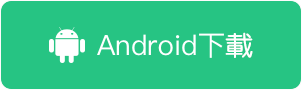「王爺,我去叫大夫給您脖子上藥吧。」
方才還不深的傷口,此時已經沁出鮮血。
就像某些傷害,總是在年深日久之後,才恍然察覺。
蕭晟旌沒有回答,神色陰鬱。
興兒順着蕭晟旌的目光望過去:階下早已空無一人,殿門打開着,只剩下一串帶血的腳印,漸漸地被嗚咽的風雪淹沒。
一夜北風之後,陰霾了許久的天氣難得露出幾分晴明。
只是無論日光如何暖融融地照在心上,對於長歡和燕國王室的人而言,都是冰涼刺骨。
七日之後便是蕭晟旌與長歡的大喜之日,燕王的喪葬之禮來不及拖延,第三日便草草舉行。
長歡一身縞素,跪在大殿冰涼的地磚上,聽着禮官的指示,僵硬地站立,屈膝,磕頭。往日與她嬉鬧的皇子公主,見了她又懼怕又諂媚,還隱隱透露出不屑。
一個禍水,讓他們落得這般田地,卻對他們不管不顧,還眼巴巴地把亂臣賊子做了夫君,風風光光地做王妃,從此養尊處優,燕王的王室,何時出現過這樣不知尊卑的東西?
「瞧她,父皇生前那樣寵她,她竟然連一滴眼淚都流不出來!」
「人家不日便要大婚了,高興都來不及,哪裡還顧得傷心?」
「真是見不得這樣的髒東西,竟然還有臉面跪在父皇的靈柩前!」
幾個皇子和後宮妃嬪跪在前面,一邊回頭打量長歡,一邊竊竊私語,有些話越說越難聽。
長歡就在不遠處,那些聲音自然是一字不差地傳到了她的耳朵里。
如此跪了整整一晚,長歡將世上難聽的詞都聽了一個遍。只是無論那些人如何咒罵她,她都不曾反駁半句,只是安安靜靜地跪在蒲團上,仰頭望着靈前的白幡,飄飄悠悠地盪着。
幾日一來,長歡心力交瘁。她原本就病着,折騰了許多天,氣力愈發不足。不過是憑着一口氣硬撐着。
勉強支撐到天明,燕王的靈柩遷入皇陵,長歡一人回到居室,回來便不斷地咳嗽,幾乎要把肺病都咳出來。
好不容易緩過來,長歡擦了擦溢出眼角的淚水,癱軟在床上,平復呼吸。
剛準備直起身,大門便被人推開,蕭晟旌一襲黑衣,袖口處繡着纏繞着的繁密花朵,腰間也用金線繡的祥雲腰帶束着,眉目如畫,玉樹臨風。
長歡立刻站起來,規規矩矩地朝着蕭晟旌行禮,也不問他來做什麼。
蕭晟旌見她如此順從,原本還算明朗的心情便增了一絲陰雲,語氣也十分不善:「既然喪事已畢,公主身上的素衣也可脫了吧?」
「是。」長歡低眉斂目,沒有絲毫異議。
蕭晟旌陡然生出無力之感,環顧四周:室內焚着檀香,清淡雅致。地上的炭火也紅紅火火地燃燒着,一室暖意。一切都理所當然,仿佛只有他,是這個房裡,極其突兀的存在。
他握緊拳頭,上前一步,聲音愈發冷硬:「既然答了是,為什麼不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