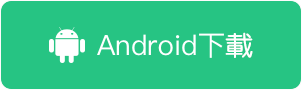蘇硯從戲班的後門入內,班主立刻拉了他道:「蘇公子,快些吧,尊王爺來了!點名要你唱戲。咱們惹不起他,你看……」
「我馬上就來。」蘇硯的聲音軟軟柔柔。
打開那木盒子,蘇硯取出那大大小小十二支刷子。
旁邊的班主忙吩咐着其他人:「快些,上妝還得要一盞茶的時候,你們快些準備戲服!」
「戲服可是好了?」蘇硯笑着扭過頭,班主看到蘇硯時,嚇了一跳。
「這……今天如何這樣快就上好妝了?」班主驚訝地看着蘇硯,目光又落在了他面前的桌子上。班主的眼睛一亮。
「喲!這是何物!這樣新奇!正是用它,上妝才這樣快麼!」班主問。
「倒是個好東西,是一位戲迷送的。」蘇硯起身穿衣,留下一臉疑問的班主。
不知為何,蘇硯第二天又去了落月糊。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居然期待見到那個女子。想來是生活太無聊了,突然有人送來了新鮮的東西,好像這日子又變成彩色的了。
這一次蘇硯沒有在船上,他坐在落月亭里,只想讓那個女子容易發現自己。
想來,他這種期待也是自欺欺人吧。她還不知道來不來呢。
蘇硯在那裡等着一天。那女子沒有再來,蘇硯竟有些小小的失望。
蘇硯起身,目光不經意掃到石桌,發現石桌的最底下,藏着一個木盒。那石桌底下本來就有雕花的裝飾,如果不是細心,又如何知道這裡還有一個東西呢。
蘇硯笑笑,俯身取了那木盒。
裡面是一套可拆卸的珍珠頭面,還有一包藥片。旁有一行小字,寫着:珍珠養人,藥可潤喉。
他相信那個女子。
字剛毅中帶着戾氣,若不是昨天見過她,他都要以為寫這字的,是個男子了。
蘇硯回到戲班便擺弄着那套珍珠頭面,他聰明如斯,自然知道這不是一套普通的珍珠頭面。
做這套頭面的人恐怕是機關大家吧。蘇硯玩着這套頭面,心裡竟埋怨起那個女子來:上妝,上頭面容易了,他可就沒有偷懶的時間了。
不知道她第三天會不會再送東西呢?
第三天,蘇硯有戲。一大清早戲園子裡便有了好多人在等着。只是這個時候蘇硯還未起床。
聽到敲門聲,蘇硯軟軟地應了一聲。門外的小子推門進來,他道:「公子,是一位姑娘送的,說是趁公子起床前送。」
蘇硯心裡一喜,想着,本來還正因為去不了落月湖而苦惱,她倒送到戲園子裡來了。
蘇硯接了那個大木盒子,在小子轉身出去之前,他問:「班主不是不會隨便收人禮物麼?如何單單收下了這一件?」
那小子解釋說:「因為那位姑娘說,公子化妝的那套化妝刷是她送的,想來公子一定會收下她的東西的。」
蘇硯一笑,那女子果然聰明。
蘇硯打開那盒子,見裡面竟是一套衣服。只是這套衣服也太過奇怪了。他坐起來擺弄着那套衣服,擺弄了一個時辰,他才知道那衣服怎麼穿,同時,他也紅了臉。
那件「小衣」竟然還有「伸縮」功能,因為是第一次見,也是第一次穿這樣的「褻衣」,蘇硯不禁有些羞澀。
其實雲靜只是用細毛線給他織了條內褲,又用細鍛子為他做了內衣長褲。自然都是貼身的。那內衣讓人用碎鐵做了拉鏈。這套衣服是讓他套在戲服裡面的。
蘇硯穿上這身衣服,又披上外衣。他突然想起自己還未成名前的一件事情來。
他是個低賤的戲子,那些達官貴人對他任意拉扯。他曾多次被人扯得露出了肩膀,那些人對他越發的不尊重。
蘇硯低頭,他試着拉了一下自己的外衣,外衣脫落,內衣緊緊貼在身上。想來,如果他早就有這套衣服,那些人便不能輕易地將他的衣服剝落吧。將那條拉鏈拉開了又提上,他第一次見這種「扣子」。
蘇硯笑笑,那個女子是天外來人麼?竟有這樣新奇的玩意兒。他是個戲子,這裡本來就是消息靈通的地方,可是與那女子比起來,他還是孤陋寡聞了。
蘇硯的心情特別好,於是今天的戲特別出彩。
墨白問雲靜:「小姐,你那樣費盡心思地送他禮物,要是我,我早就感動了。」
雲靜輕聲道:「他是個戲子,是看慣悲歡離合,也看得穿逢場作戲。如果送他的禮物不是新奇的,也不討他喜歡的話,他根本就不會看一眼。」
墨白點頭,臉上卻是似懂非懂。
雲靜和墨白再一次進了慶和戲園,這一次她一去,便有人請她到了後台。
蘇硯在後台那裡等着她。
雲靜一臉漠然。她不是他的戲迷,她只是想利用他。
他沒有同語珏漂亮,也不若穆千塵冷冽,他有的,只是眼裡的一灣死水。他只留了這個身子在世子,靈魂早就飛去佛祖那裡了。
所以,雲靜見到蘇硯時,沒有歡喜。
所以,蘇硯有些意外。
「有一個人想見你,我與她有些交情,所以才這樣做。」雲靜說。
蘇硯聽雲靜這樣說,竟然有些失望。
原來她並不因為喜歡自己才這樣做。竟是為了別人。可,卻又是什麼樣的人讓她這樣如何費盡心思呢?
「雖然姑娘是他人對我好的,可我依然欣喜。」蘇硯垂首低笑。
雲靜不是冷血的人,她的冷血只對她的仇人。所以雲靜便說:「她叫做秦可兒。」
蘇硯一怔,他抬頭看雲靜:「是她。只有她才會這樣做吧。是不是她苦苦求你討我的歡心?又苦苦求你一定要帶了我去見她?」
這一次,輪到雲靜驚訝了。原來他們不是一對怨侶。原來只是秦可兒單戀着蘇硯。
雲靜搖了頭道:「沒有,她沒有求我,只是我感覺你與他雖然表面上看破紅塵,可是心裡卻還是渴望着一次悲歡離合。有過了,就算是到最後悲傷不已,也是自己的收穫。」
蘇硯笑着,可雲靜的眼神穿過他的笑,看到了淒涼。
「她想念我麼?只可惜,我想念的不是她。」蘇硯的手撫上自己的衣服,在拉鏈的頭處摩挲着。
雲靜沒想到蘇硯竟說的這樣直白。
「她也是身不由已,你總要給她一個活着的念想吧。」雲靜靠近了蘇硯,蘇硯身子一僵,似是想躲開她。
「我給了她念想,誰來給我念想……」蘇硯低聲說。
雲靜不作聲了。
「你說吧,什麼時候,什麼地點,我去見見她。一年不見了,不知道她有沒有長高。」蘇硯說。
雲靜淺淺一笑:「多謝蘇公子,回頭我會讓墨白告訴蘇公子的。」
蘇硯知道雲靜這樣說了就是要離開了,他心裡湧起一股失落。
「我送你離開。」蘇硯說。
蘇硯走在雲靜的身後,雲靜停了腳步問他:「蘇公子在為難什麼?」
蘇硯一怔,問:「姑娘為何這樣問?」
「要不然,蘇公子為何總是走在雲靜身後?」雲靜問。
蘇硯又是一怔,隨後又眯了眼睛笑了:「蘇某隻是一個戲子,不能與小姐並肩而行。」
墨白插了一句:「我家小姐是武林中人,沒有那些繁文縟節的,公子再這樣,我家小姐會生氣的。」
蘇硯瞄了雲靜一眼,雲靜微憨。
蘇硯與雲靜並肩走出後台,兩個人往後門去,剛走幾步蘇硯又停住了。
雲靜看了蘇硯一眼,見他平淡如水的眼裡起了一層波瀾。再看看他的身後,有一個蘭衣男子正一邊呼喊着一邊往這裡來。
「喲!這不是趙家的四公子麼!」
另一個紫袍男子往這裡看,然後張口就罵:「他可不是我趙家的人,誰知道他是誰家的雜種!」
蘭衣男子大笑,他高聲道:「趙兄,你怎麼能這樣說,他可是上了趙家的族譜的!」
紫袍男子冷哼:「早就除名了!」
蘇硯閉了眼睛,胸脯劇烈地起伏。他是不在乎族譜上有沒有他的名字的,但那是他母親用生命換來的,那,他就要在乎了。
蘇硯猛得轉身,卻被雲靜一把拉住。蘇硯看向雲靜,雲靜卻是淡然地看向了那個紫袍男子。
紫袍男子也看到了雲靜,他冷笑起來:「還做了人家的小白臉,真是有本事啊。」
蘇硯見雲靜要動,他忙拉了她道:「雲姑娘,蘇某一介戲子,不值得。」
雲靜扭頭沖蘇硯道:「知不知道什麼叫做打狗看主人?人賤不賤可不是他人說了算。難道這位趙公子敢說皇上近前的公公是閹人麼?除非他九族是活得不耐煩了。」
墨白笑出了聲。
雲靜走到了紫袍男子的面前,紫袍男子比雲靜高上半個頭,他居高臨下地問:「你是哪裡來的野丫頭?要為別人打抱不平,也不打聽打聽本公子是誰?」
雲靜淡淡地道:「你不就姓趙麼?你莫非是敬國公趙醒?可趙醒沒這樣年輕啊!」
紫袍男子聽了雲靜的話,心裡便發虛了。她能輕輕鬆鬆說出敬國公的字號來,就說明她比敬國公的地位要高,更何況,他只是敬國公家的遠親。
看着男子的臉色,她便知道他不是敬國公的人。
雲靜道:「向這位蘇公子道歉,要不然你家突然被人滅了門,你會後悔的。」
蘭衣男子早就不敢再說一句話了。紫袍男子只好向蘇硯作了揖道:「是在下無禮,望蘇公子海涵!」
「我們走吧。」蘇硯只說了一句。
雲靜轉了身與蘇硯一起,蘇硯扭頭看向雲靜,他輕聲說:「我本來不在乎名份,可那個名份是我娘用命換來的。她死的原來這樣不值,也原來在他們眼裡,人命是如此之賤。」
雲靜心裡一動,無來由的,她竟想起了自己家的那場大火。
蘇硯的娘只是一條人命,她家與方圓幾里的村子何止是一條命!
雲靜的周身散發出了戾氣,蘇硯被唬得說不出話來。
紫袍男子正站在原地狠狠瞪着雲靜的背影,雲靜突然轉過身來,他也被嚇了一跳——那目光好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