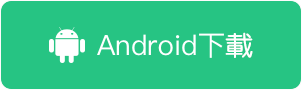祈驚闕掌管着刑部,先皇在世的時候,他建立了一個介于禁衛軍和正統軍的酒肆衛。
酒肆衛隸屬先皇和祈驚闕掌管,作用是解決不了刑部,以及先皇辦不了的隱晦之事。
祈驚闕為人乖張,陰鷙,陰晴不定,只要到了他手中的犯人,沒有一個人能扛住三天不吐露真言,更沒有人能在他手上吐露真言之後,還能活着出酒肆衛的。
我眼紅他的酒肆衛,暗中與他交手幾次,想着從他的手上拿回酒肆衛為我和赫連決所用,可都以敗北而終,而他不對我下手的原因,大抵是因為我的父親是一品軍侯,曾經有恩於他。
但我覺得他留不得,暗地裡不止一次的跟赫連決說,祈驚闕就算是太監,越早除去越好,留着終究是禍害。
沒想到,赫連決沒有把他給除掉,而把我先給除掉了,更沒想到,我會在這滿是屍體的亂葬崗,碰見這尊煞星。
鏘!
一聲劍抽出劍柄聲音炸在我的耳邊。
我的手狠狠地抓在地上, 指腹抓出了血,努力的睜眼視線上調,看着祈驚闕絕艷雌雄莫辨近妖治的臉,心中一橫,鋌而走險張口道:「九千歲,我受過皇后娘娘的恩典,不忍見皇后娘娘屍體沉於冷宮荒院,故來此送娘娘一程,絕無衝撞之意!」
我的話音一落,祈驚闕眼神幽暗深不見底,嘴角勾起一抹嘲諷的弧度,「一個識人不清蠢到極致的女人,還有人冒大不韙送她一程,這倒真是稀客啊。」
無暇顧及我怎麼成了他口中蠢到極致的女人,為了活着,我謊話信口拈來:「我初入宮廷,被人欺凌,是娘娘出手相救,九千歲,您若殺我,請讓我安葬了娘娘,您再動手!」
祈驚闕幽深如淵的黑眸兇殘嗜血陰森詭異的盯着我,聲音更是冷漠到極致:「你在說謊,那個無利不起早的女人,從來不會出手去救一個對她無用之人。」
都說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我活着的時候視他為死對頭,要除掉的對象,想來他也如同我一樣,想把我弄死,所以才會如此了解我。
「我沒有撒謊!」我胸口起伏,脖子上懸的利劍,讓我急切地說道:「皇宮內院,妃嬪眾多,娘娘需要安插眼線,掌握各宮小主的動向,我就是娘娘安插在宣和宮的人。」
「九千歲您若是不信,可以去宣和宮詢問,若是奴婢撒謊,自願去酒肆衛領罰!」
祈驚闕漆黑的眸子深不見底,盯着我不語,我額頭上的冷汗滑過,我在賭他還記得欠我父親的恩情,繼而我收屍,他能放過我一馬。
他盯着我,再我以為他不會說話的時候,他手微微一抬,踩着我臉頰的人把腳鬆開。
當然我不會天真的以為以他的性子,就這樣輕而易舉的信了我,緊繃着神經目不轉睛地回望着他。
豈料!
他頭一扭,目光凝視着深坑,仿佛一眼萬年,坑裡有他最捨不得的一往情深。
「是嗎?識人不清的女人,臨死之前倒養了一條好狗。」祈驚闕嘴角露出一抹冷淡的嘲弄,言語多刻薄。
他的話讓我無法去接,赫連決把我殺了,眾叛親離,沒有人給我收屍,我只有我自己。
巨大濃重的悲悸划過心間,瞧着風颳起祈驚闕紅色的衣袍帶動着飛沙咧咧作響,一時間,他俊美如妖孽的臉恍若如仙人,從天而降,跳進了我埋屍體的坑裡。
我心中驚悚,連忙趴在坑沿邊張望着他,只見他小心翼翼脫下外袍,不嫌骯髒的把我沒有四肢地屍體包裹在他的外袍里,如獲珍寶般抱在了懷中。
我的眉間狠狠的跳動了一下,想笑笑不出來,原來替我收屍的人,是我一直想弄死的死對頭。
而我最愛的人,連具全屍都不給我,只讓我拋屍荒野,做孤魂野鬼。
祈驚闕確定屍體沒有在他的衣袍外,縱身一躍跳的上來,我沒來得及躲,他一腳踩在我的手背上。
居高臨下的用力碾壓着,聲音冷漠如狼似虎:「你口中所說,我會查清楚,若有半句虛假,猶如此指。」
祈驚闕話音落下抬起腳,直接踩斷我的小拇指,疼痛讓我慘白了臉,慘叫一聲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