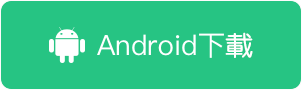騎在我身上的人,用力的掐着我的脖子,對面的人還在吶喊:「殺了她,我們這裡又多了一分勝算!」
吶喊聲和窒息驚起了我,不再去看祈驚闕,我要活着,必須要殺人。
手中是刀多多塞給我薄如蟬翼的刃,開始腿腳掙扎,我的掙扎驚起鐵籠子裡更多的人吶喊,他們像瘋了一樣,不斷的吶喊助威,似殺了我,他們就能得到自由一樣。
掐住我的是一個黑胖的女人,女人披頭散髮,眼中凶光四射,咬牙切齒,口水滴在我的臉上。
我手中薄如蟬翼的刀刃,輕輕一揮,對着黑胖的女人脖頸動脈劃了過去。
鋒利的刃,切出一道紅印子,血跡濺到我的嘴邊,像從地獄爬出來的惡鬼,只想殺人喝血泄憤。
黑胖的女人雙眼出現一絲錯愕,掐住我脖子的手鬆開,扣在自己的脖子上,企圖去捂住流血的脖子。
我腿上一個用力,把黑胖的女人掀翻在地,剎那之間,鐵籠子的吶喊聲戛然而止。
我從地上翻起來,手緊緊的握着薄如蟬翼的刃,雙眼滿是戾氣看着地上黑胖的女人和對面的人。
黑胖的女人瞳孔驟然緊縮,伸手對着對面人,張嘴向他們呼救:「救我……救…救我……」
然而對面她呼救的人,表情木訥,眼中全是嗜血光芒,齊刷刷的望着我,似在打量着我的全身,想着從我身上哪裡下手比較好?
鮮血流了一地,黑胖的女人做着哀求呼喊的姿勢死在鐵籠子裡。
對面呼叫吶喊的人都沒多餘看到黑胖女人一眼,死,他們仿佛習以為常。
我細細的打量着對面對峙之人,上了年歲的兩個,四個男人,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一個臉上滿是污穢的女人,總共八個人。
我的腦子裡浮現着刀多多臨走之前說的話:「活了,就能離開,死了,就如糞便一樣處理。」
他的意思,我要活着,就能離開這裡,死了,就跟這裡的糞便一樣,臭氣熏人,只要配水一衝,什麼痕跡都不會留下來。
餘光再看向祈驚闕所在之處,發現他的人早已不見,四周鐵籠子外面守着的太監,拿着鐵棒,敲在鐵籠子上,鐵籠子裡的人,開始躁動起來。
就連我所處的這個鐵籠八個人,也像一池驚了的魚,本來還相互靠攏,一下子四處逃竄,各自為營占據籠子一角,相互敵視對望。
我也如同他們一樣,弓着腰,彎着腿,背抵在鐵籠子上,做着既能防禦又能攻擊的姿態。
「啊!」
一聲撕心裂肺的尖叫嘶吼,打破了地牢的安靜,讓地牢里所有鐵籠里的人,都瘋了一樣,拼命地向對方撲去,不死不休。
向我撲來的是那個十二三歲的孩子,他瘦骨如柴,眼睛突兀,手勁很大,抓住我的手就咬。
只有一瞬間的遲疑,我比他們赤手空拳多了一把刃,削鐵如泥的刃對着咬住我的那個小瘋子,毫不客氣的對着他的割去。
他眼睛瞪得跟銅鈴似的,緊緊抓住我手腕的手,到死都捨不得鬆開。
我用力一掰,把他的手掰離我的手腕,頓時之間,我的耳邊一片殺聲嘶喊。
我加入他們的混戰之中,大家都沒有拳腳功夫,拼的就是誰不要命,誰更兇狠?
我的腦子裡不斷的回想着赫連決,不斷地想着姜媚兒,不斷的告訴自己,不能就此死去,必須要活着出去,不能像糞便一樣,隨便一桶水就能沖刷。
不要命的我,直致精疲力盡,滿身傷痕,看着鐵籠里的九具屍體,用手背抹了一把嘴角,滿嘴的血腥味,令人犯嘔的想吐。
鐵籠子的門鎖住的鎖不知何時被解開,一推就推開了,每個鐵籠里只走出來一個人,跟我在內,也就七個人。
我們七個人狼狽至極,刀多多出現了,對着我們七個人吐出一個字:「來!」
在別人警惕面面相覷之時,我第一個抬腳跟着刀多多走,自己的血和別人的血交織在一起,滴滴嗒嗒地隨着我的腳步拖了一地。
來到一處深井邊,和其他的人站成一排,一桶桶涼水向我們潑來,毫無尊嚴的洗刷,變回人樣。
而後男的關在一間屋,女的關進了小黑屋裡,烏漆嘛黑的屋子伸手不見五指。
我剛扶着牆壁,慢慢的滑靠坐下來,隔壁關着男人的小黑屋,就傳來撕心裂肺的痛哭聲。
伴隨着痛哭謾罵和詛咒聲,原來活下來的男人在隔壁行閹割之事,做太監。
震耳欲聾的哭喊,迴蕩在漆黑的黑屋裡,我迸住呼吸,渾身緊繃,用紅腫疼痛的手指敲擊在牆上,計算着時辰。
一個時辰,兩個時辰,一天,兩天,度日如年,不見光亮,沒吃沒喝,每當我快要撐不住睡意之時,我都會用手中的刃割開手臂,用疼痛來抵消睡意。
第三日光亮刺眼,飢腸轆轆,走路腿都打着飄,我的手臂上,已經乾枯了好幾道傷痕。
刀多多出現在門口,什麼話也沒說,帶着我們一行人,離開了小黑屋。
直致上了一輛華麗的馬車,我心裡慌了,我不知道他們會把我帶到哪裡去,我不能離開,離開皇宮靠近不了赫連決和姜媚兒我就報不了仇了。
急忙撩起車簾,對着要驅趕馬車的刀多多迫切的問道:「公公,咱們這是要去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