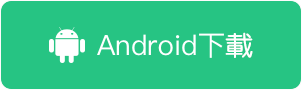「淨世聖子……」白阿喃喃念叨,眼中神色迷離,也不知在想些什麼。
沉默了一陣,齋殤繼續說道:「這些年我和你爺爺查了不少有關天之詛咒的書籍,多少也掌握了一些解除詛咒的方法。本來我們是不想讓你參加祭天的,畢竟不管再如何縝密的計劃也不可能做到沒有一絲漏洞,但天光洗禮對解除天之詛咒有着莫大的好處,所以你爺爺經過一番慎重的考慮之後還是決定讓你去參加此次的祭天。等你經過天光洗禮之後,我們便馬上找機會為你解除天之詛咒。」
白阿皺着眉頭問道:「可是經過天光洗禮後的人不是馬上便要前往天都嗎,到時候哪裡還有機會避開其他人解除天之詛咒呢,而且到時候羽央尊者可是也在場的啊?」
齋殤擺手說道:「這你不用擔心,我和你爺爺會安排好一切的,你只要好好接受天光洗禮便行了。今晚你好好休息一下吧,明天我便竭盡全力用丹藥鎮壓住天之詛咒,讓其在短時間內對你的影響減小到最低點。然後再利用藥陣法暫時提升你的修為。整個過程可能會有些痛苦,你要忍耐一下。」
「嗯……」白阿輕輕點了下頭,眼中神色不斷變幻,似乎在思考着什麼,並沒有將齋殤口中的痛苦放在心上,經過這些年天之詛咒的折磨,他對所謂的疼痛早已麻木了。
齋殤靜靜的看着白阿,欲言又止,最後說了句早點休息,便閃身消失在了原地。
月光輕柔,九天垂灑,落在他的臉龐。那一雙明亮的眼眸之中,閃射出一股複雜的神情。他猛地抬頭,望着漫天星辰,不顧冷風放肆的喧嘯,高舉修長的手臂,明問蒼天:「為什麼,你為什麼不容許我來到這個世上,難道我對這個世界而言真的是一個妖孽嗎……為什麼……」
聲音悠悠,和着如水的月華傳上天際,卻換不來蒼天絲毫的回應。最終,他還是只能孤單單的一個人離開了屋頂,依如從前的身影……
第二天清晨,白阿剛剛用完早餐,北宮啻和齋殤便帶着一群黑袍強者來到了永恆山上。時隔十八載,北宮啻的樣貌並沒有發生多大變化,依舊是一副仙風鶴骨之態,只不過那一雙銳智的眼睛中所散發出來的光芒越發顯得凌厲了。
「孫兒見過爺爺。」白阿對着北宮啻彎腰行禮道。
「嗯,昨天齋殤也把一切事情都告訴你了,你如今可準備好了?」北宮啻看着白阿淡淡說道,仿佛是在說着一件毫不相關的事情,但那眼睛深處卻自有一絲隱晦的慈祥之色一閃而過。
白阿早已習慣了北宮啻這樣看似冷漠的說話方式,也不在意,只是淡淡一笑道:「嗯,孫兒已經做好心理準備了。」
「好,身為我北宮族的男兒就該當這般果斷,你先換上這件祭天袍吧。」說罷北宮啻右手一招,一件散發着高貴氣息的長袍便憑空出現在了他的右手之上。
白阿神情恭敬的伸出雙手接過祭天袍,對於這件傳說中由天恩賜給四大守天族的祭天袍,白阿心中不敢有一絲褻瀆之意。如今現存於世的祭天袍也只有他手中的這件和軒轅族保管着的那件了,其餘的都早已在兩千多年的護天之戰中損壞。
不過一會功夫,白阿便回房換上祭天袍重新走了出來。但見他銀髮飄揚,目光炯然,身上祭天袍那淺綠色的紋帶勾勒出一股古老而神聖的氣息,胸前的祭字圖紋更是散發出一股仿佛渾然天成的大道氣韻。白阿整個人乍看之下,竟讓人有種仿佛回到了洪荒時期看到遠古祭祀的感覺。
看着眼前神彩飄揚的白阿,在場的所有人包括北宮啻在內,竟忽然同時有了一種奇怪的感覺,仿佛這件祭天袍本來就是為白阿量身定做的一般。
「隨我來吧。」北宮啻對白阿說了一句,隨即便轉身向永恆山之峰的山頂走去。
「是。」白阿應了一聲,隨即緊隨北宮啻一行人走去。
永恆峰頂,正有數十名黑袍修士圍繞着一口三丈方圓的藥池忙碌着。整個藥池的周圍都紋刻滿了複雜的陣紋,十幾名強者正站在對應的位置催動着整個陣法的運轉,不時有黑袍修士往藥池內扔下各種珍稀的藥材,在陣法的催動下,整個藥池中的藥水正不斷沸騰着,飄散出股股濃郁的藥味。
白阿站在藥池旁邊,定定看着那口沸騰的藥池,心中不知在想些什麼。
「好了,藥陣已經全面催動起來了。」齋殤忽然淡淡了說道。
北宮啻點了下頭,隨即轉身望着白阿道:「想要解除天之詛咒,你便必須走進那藥池吸收萬藥之力,而這僅僅只是解除天之詛咒的第一步,你如今還想要繼續下去嗎?」
在這個時刻,白阿竟是輕輕一笑,儘管笑容之中有着一絲勉強,但那眼中所閃射而出的偏執卻是如此狂熱。
「只要能解除天之詛咒,孫兒願受任何苦痛。」
「好,既然你有此決心,那我這個做爺爺的自然也不會讓你失望。」北宮啻難得的露出關愛之色拍了拍白阿的肩膀,隨即轉頭看向齋殤。
齋殤會意,對白阿說道:「白阿,雖然這藥池在藥陣的催動下已經徹底沸騰,但你的身體多年來一直服用靈丹妙藥,區區一點沸水是無法破壞你皮膚的。不過,相應的疼痛你還是能感受到的,所以你等一下一定要堅持住。記住,在我說好之前你絕對不能離開藥池,否則一切都可能將前功盡棄。」
「我知道了,我會堅持住的。對了,我身上的這件祭天袍要先解下來嗎?」
齋殤搖頭道:「這倒不用,你爺爺來之前已經將祭天袍的避水之能暫時封印住了,不會影響到你的身體吸收藥力。」
「嗯……」白阿點了下頭,隨即深吸了口氣,一步一步緩緩向前方的藥池走了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