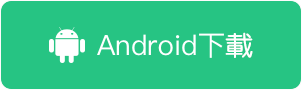本來打算今晚趁着高興,把張靈灌醉給她開苞,卻因為她非要去接張狂而耽擱到現在,一想到這兒王威的心中就甚是不爽。
「靈兒?你也配喊靈兒?」
嗙啷!
手中酒瓶磕在桌角上瞬間粉碎,望着張狂手中銳利的玻璃瓶茬,老三老四立刻警惕起來,而包廂裡面坐着的幾個青年也是瞬間站起身來,不知從何處摸來鋼棍砍刀提在手中,頃刻間便把張狂圍了起來。
「看來她已經把什麼都跟你說了,我也就懶得再跟你廢話了!」
一抬手示意手下人不要輕舉妄動,重新坐回沙發,笑盈盈地望着張狂,只聽王威繼續道:「識時務者為俊傑,張狂!我念你對我有恩,所以沒把你徹底留在裡邊兒,你不要不識好歹!」
「張……狂,威哥現在跟着修總混,不是你能得罪得起,快給威哥賠禮道歉興許他還能放你一馬!」聽到王威這話,老四連忙俯身勸道。
然而,對於他這話,張狂卻是置若罔聞。
「我今天晚上來不為其他,只為殺人!不想死的,現在可以退出去!」
聽到張狂這話,那幾個女孩立刻逃離似的一般離開了包廂。
冷酷的目光一掃全場,見其餘人沒有要離開的意思,張狂的嘴角不禁浮現出一抹嗜血的光芒。
如此最好,他也就不用念及往昔的兄弟情份了!
「動手!」
看到張狂這招牌式的笑容,老三立刻知道不妙,不待王威發號施令便率先動手,其他人也是緊隨而至。
可惜他還沒碰到張狂,便覺得脖子一涼,璇既便一頭栽倒在地上。
噗!噗!噗!
沒有絲毫多餘的動作,每一次划過都會濺射起一道血光。
能夠把殺人當作藝術,普天之下恐怕只有他張狂一人了!
當張狂丟掉沾滿鮮血的碎酒瓶時,在場中唯一還在喘氣兒的,就只剩下王威一人。
望着宛如死神一般的張狂,王威的眼神中充滿了驚恐之色,拼了命的想要躲,想要逃,但卻動彈不得。
這個時候他才駭然地發現,自己手腳筋竟然不知何時已經被張狂割斷!
張狂跟老頭子學會得,不僅僅是醫術,更有殺人的藝術!
精湛的醫術反過來用就是殺人的技藝!
很明顯,張狂把這份技藝發揮的淋漓盡致。
望着俯身過來,離自己越來越近的那張似笑非笑的臉,就好像是看到死神離自己越來越近,「張,狂狂哥……別殺我,我可以給你錢,給你很多很多錢……」
聽到王威這話張狂就笑了!
放聲大笑!
搖了搖沾滿鮮血的食指,「可我不需要錢!」
見張狂沒有直接動手,王威心中不禁鬆了一口氣,下意識問道「那你想要什麼?」
聞言,張狂又湊的更近了些,一張笑眯眯的臉龐,看起來人畜無害,但只有王威心裡最明白,當張狂顯露出這個笑容的時候,意味着什麼!
「我想要你的,命!」
嘎吧!
話音落,骨頭碎裂的聲音也隨之響起,表情最終定格在驚恐之中,原本平躺在沙發上的王威,此刻臉也是朝向了沙發墊。
「啊……你你你,你把他們全殺了?」
就在張狂剛準備起身離去的時候,門口忽然傳來一陣驚懼的尖叫聲。
望着跑出去的一眾女孩,修之涵的好奇心也愈發濃重,悄悄走過來卻恰好看到張狂扭斷王威脖子這一幕,當即被嚇得失聲尖叫。
下一刻,修之涵整個人便被張狂拽入包廂中。反腳一踢門便被關上。
「唔……嗚嗚嗚……」
整個人被張狂死死地抵在牆上,因為嘴巴又被死死地捂住,修之涵只能發出嗚咽的掙扎聲,眼神驚恐地望着張狂的眼睛。
從未有這麼一刻,死亡離自己這麼的近!
殺人滅口!
感受到張狂另外一隻手捏在了自己的脖子上,眼神瞥向沙發上已經斷氣的王威,修之涵就想到了自己的結局。
殺還是不殺?
望着手中眼神驚恐的女孩,張狂不禁猶豫起來。
他殺王威這些人是為報仇,可手中的這個女孩卻是無辜的,張狂雖然自認不是什麼好人,但讓他殺一個無辜的人,他那唯存不多的良知卻過意不去。
就在這個時候,包廂外的過道里突然一陣騷動,原本音樂聲嘈雜的酒吧也安靜下來,璇既耳畔便傳來一陣陣若有若無的警笛聲。
嘭!
就在這個時候,房門被人一腳踹開。
「裡面的人……嘔……」
兩個穿着制服的警員話還沒有說完,便忍不住捂着嘴巴嘔吐起來。
「隊長隊長,這邊有命案!」
反應過來的兩個警員立刻警動起來,一個召喚同伴,另外一個則是掏出槍來,神色緊張地指着張狂。
「放開那個女孩,把手舉起來!」
張狂雖然自負,但還沒自大到想要以血肉之軀對抗子彈的地步,況且他也不想那麼做。
「嗚嗚……」被鬆開的修之涵慌不擇路地跑了出去,而這個時候其他警力也紛紛趕來,把最裡面這間包廂圍了個水泄不通。
「什麼情況……」
領頭的是一個英姿矯健的女警官,剛準備詢問情況不小心瞥了一眼包廂裡面的景象,差點兒沒吐出來。
「人是你殺的?」
「帶走!」見裡面的人不說話,這個女警官也不多說廢話,立刻示意手下把張狂銬起來帶走。
江城治安局,審訊室外。
「司長,王威死了……」撥通了上司的電話,紀勝男的臉色鄭重不已,發生了這麼大的案件,一旦傳揚出去,絕對會鬧得滿城風雨人心惶惶,這絕對不是她上司願意看到的局面。
「什麼?居然會發生這種事?先處理現場,把事態壓下去,等我電話!」說着那頭便掛斷了電話。
收起手機,紀勝男這才踏入了審訊室,仔細打量起端坐在審訊椅上神態自若的張狂。
紀勝男怎麼也無法想象,一個人究竟得有多麼強大的內心,才能在親手了結了那麼多生命之後,還能如此鎮定自若地坐在那兒,宛似一個無關者一般。